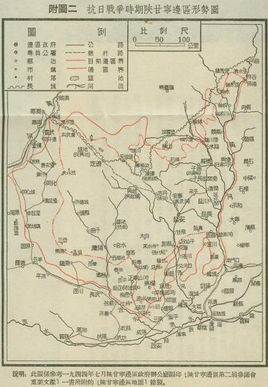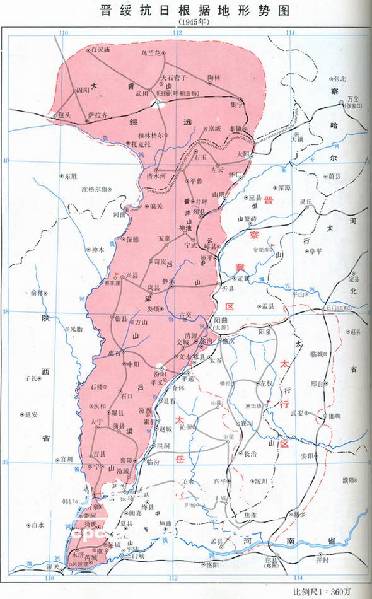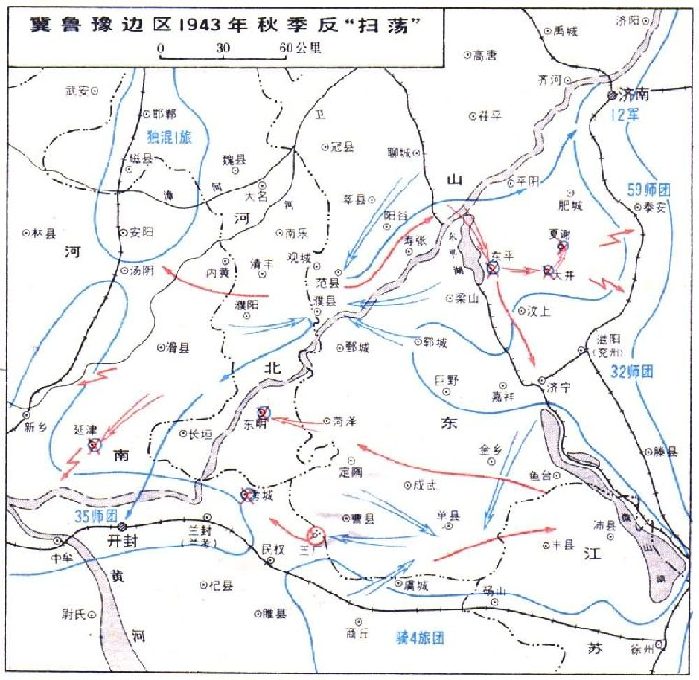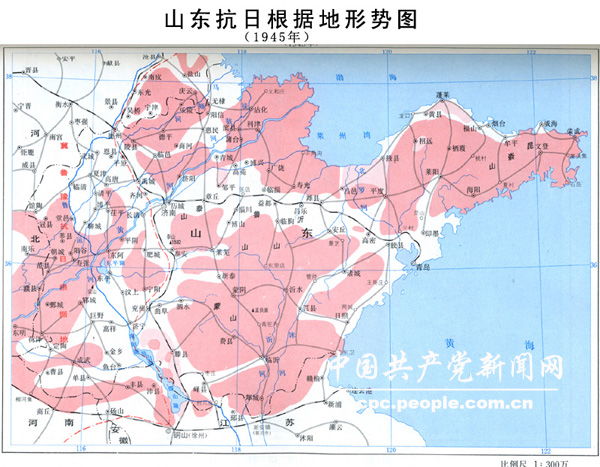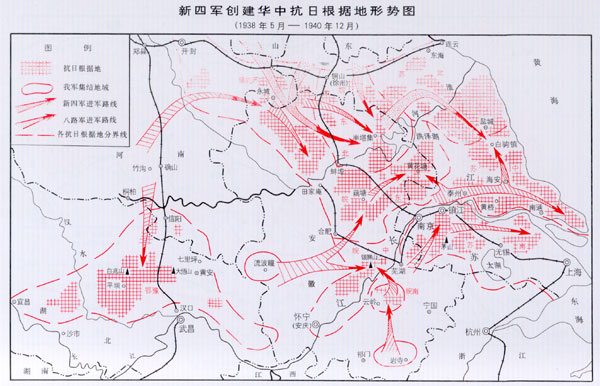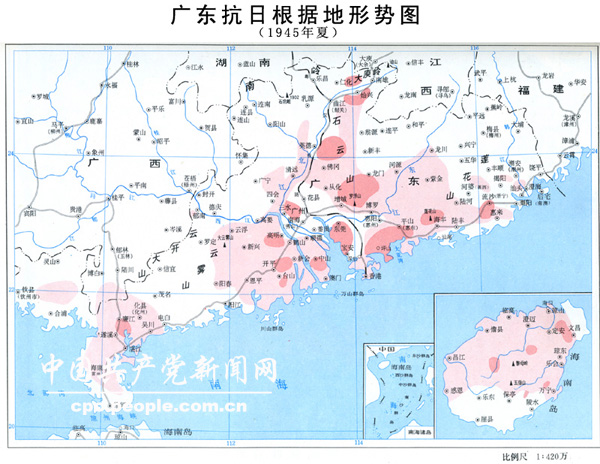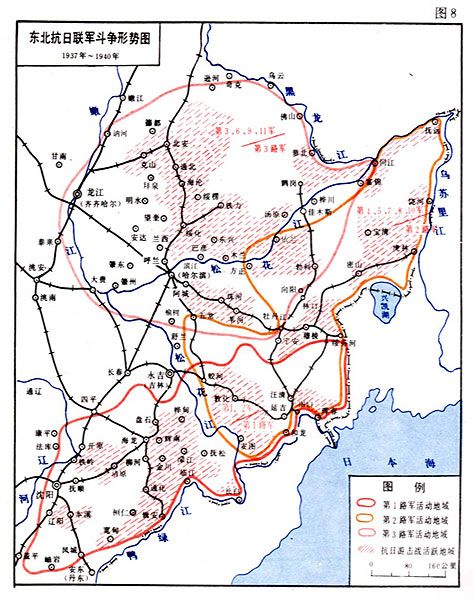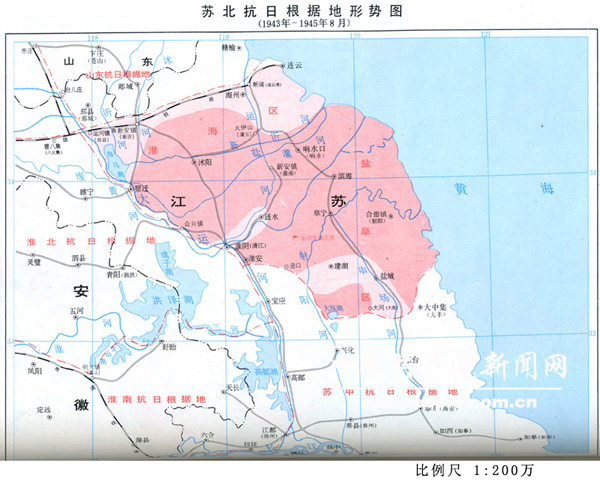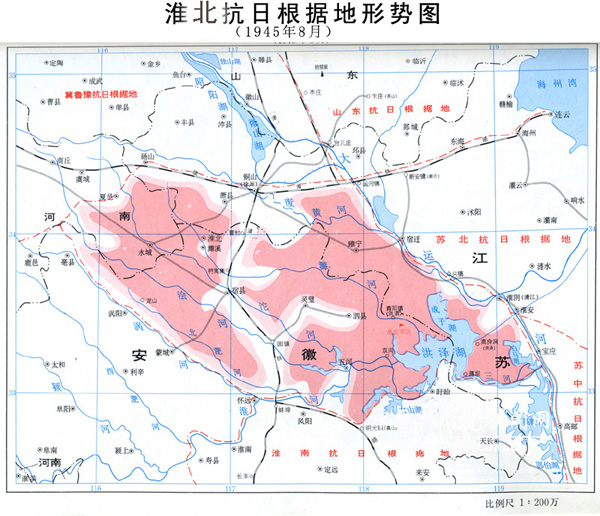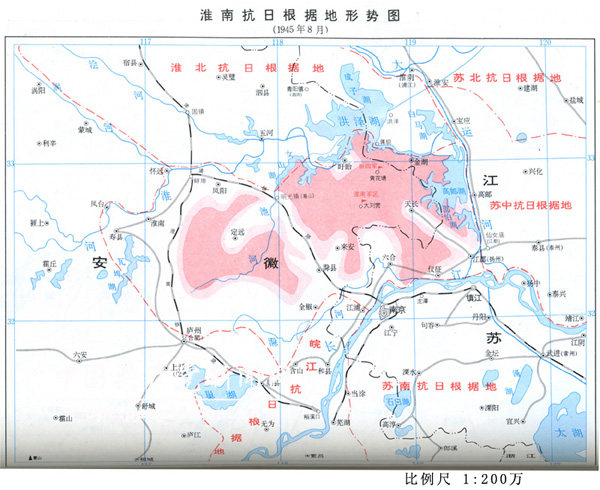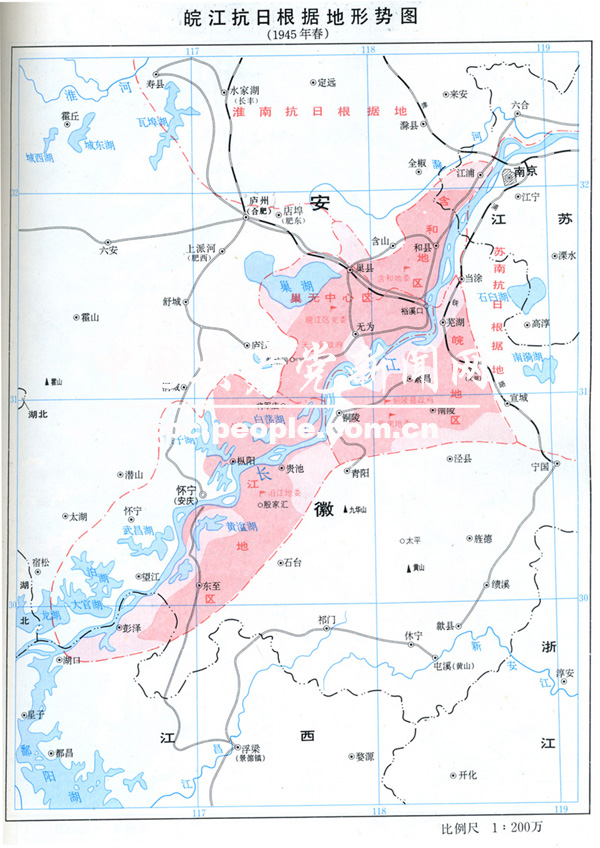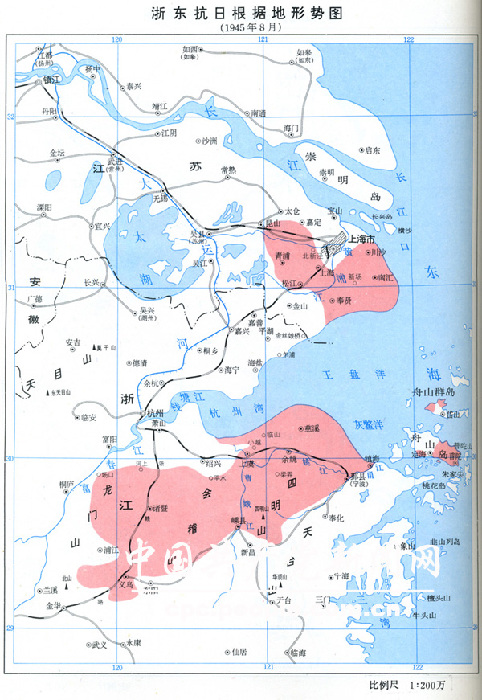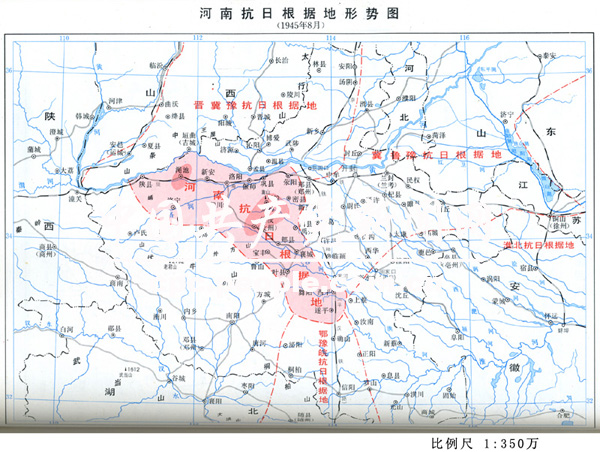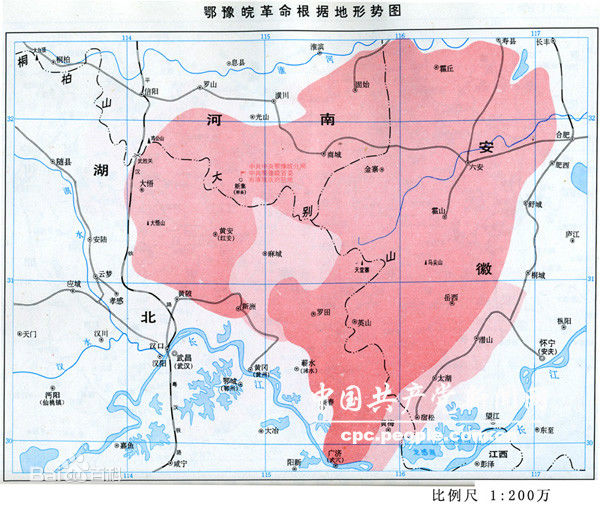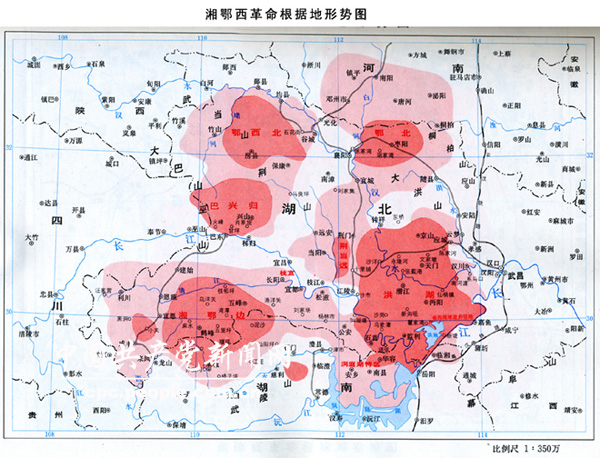|
|
|
《昨天的中国》(法)阎雷(Yann
Layma)著杨宁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年3月定价:128.00元
|
文/那日松
编者按:阎雷(Yann
Layma),1962年生,法国著名摄影师。1985年,阎雷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首次来到中国,30年来共拍摄了60多个关于中国的摄影报道,出版了4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他的大型摄影集《中国》于2004年在全世界6个国家同步发行,印量达几十万册,这也使他成为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中国题材摄影师。《昨天的中国》以阎雷的大型摄影集《中国》为底本,甄选并增补部分未公开发表的照片,重新编排成册,全面呈现1985—2000年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日常生活、经济起飞和社会巨变,用镜头为整个中国创作一幅最鲜活、最富生命力的肖像。
作者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三十年间足迹踏遍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敏锐地捕捉到这个具有厚重色调的国度在20世纪末对变革的渴望、对新鲜事物的痴迷,通过他的视角,将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微妙和激烈之处真实地传递出来,真实展现了那段逐渐远去的历史。
1
阎雷其人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如果你在北京某一条大街或者胡同里,见到一位身上挂满“莱卡”相机,脚蹬变速车,脸上扣着防毒面具的“老外”在那里东张西望,时不时“摄”两下的,那可能就是阎雷。
阎雷—YANN
LAYMA,1962年出生,法国布列东人,属于法国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的共同特点是头发黄,性格固执,喜欢离家出走。阎雷无一例外地全部继承了这些传统。从14岁他就开始周游世界,16岁喜欢上了摄影,18岁成为了职业摄影师。1981年,他19岁的时候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他总共来过中国多少次,他早已数不清。他的第一位妻子,就是一个四川姑娘。
阎雷最爱吃的中国菜是“宫爆鸡丁”和“糖醋里脊”,属特平常的两道菜。
阎雷的汉语说得非常好,与他交流不会有什么语言上的障碍。每当有中国人夸他汉语说得好时,他总是很“谦虚”地说:“一般吧,比你好不了多少。”据说有一次他到一个中国餐馆吃饭,服务员见是一个外国人进来,便互相小声说:“来了一个老外,宰他一顿。”阎雷听见后,大声说:“你才是老外,想宰我,没门儿!”
这就是阎雷,其实2007年才45岁,自称属虎。
在以中国为主要拍摄题材的当代外国摄影家中,阎雷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最优秀的之一。虽然,国内的报刊很少有关于他的介绍,他的作品也很少在国内发表过。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会。
2004年10月,阎雷的《巨龙108像—20年摄影中国》摄影展在法国巴黎卢森堡公园展出,108张1.8米×1.2米的巨幅照片沿公园的栅栏墙排开,成为巴黎最耀眼的一道风景。
他的大型画册《中国》也在全世界7个国家首发,首印数量就达到30万。
同一年10月,阎雷还参加了在北京故宫举办的《紫禁城国际摄影大展》。
阎雷不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也不自称是艺术家,他只拍他认为很美的“故事”,如果我们经常留意国外的杂志,比如德国《地理》、法国《地理》等,你就会发现很多阎雷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照片。当然,阎雷并不仅仅拍中国,他已经采访过80多个国家,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路上,而全世界像他这样成功地为杂志拍“故事”的摄影师并不多,据阎雷自己讲,能够经常在杂志上见到名字的摄影师不超过150个。有一点,也许可以说是遗憾,那就是阎雷没有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过,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不大喜欢现在的《国家地理》,更重要的是他无法与那些高傲而唯我独尊的编辑们一起工作。
我第一次认识阎雷还是1993年在台湾阮义忠先生主编的《影像杂志》上,他的名字被译成扬·雷马,那是一篇关于巴比雍(大陆译作波佩尼昂)报道摄影节的专题报道,文中提到一位因拍摄中国云南梯田而成功的法国摄影家—他就是阎雷。
后来在德国地理杂志上我终于看到了完整的《山的雕刻者》(即那组在波佩尼昂取得重大成功的照片故事),确实非常出色,令人拍案叫绝。我们国内也有无数的摄影师拍过梯田,但基本上都差不多,从来没有人深入进去;阎雷不同,他从“宗教”入手,从哀牢山人对大米对水牛的崇拜入手,把山、水、大米、水牛、哀牢山人、巫师、图腾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展开画面,图片精彩,文字也很漂亮。
1996年,我作为《大众摄影》杂志的图片编辑,曾“盗版”(阎雷的说法)选用了他的部分图片,并翻译了故事的全文,刊登在《大众摄影》上。
2
共赴三江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
1998年3月26日,在北京,我终于见到了阎雷。这次我是奉中国摄影家协会国际部的指派,陪同阎雷一起赴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为期半个月的采访,题目是“侗族妇女”,是专为德国《妇女》杂志拍摄。到达三江的还有一位《妇女》杂志的女编辑—艾克,严雷管她叫“可爱”。
关于“侗族”的专题,是阎雷10多年前就拍摄过的。他这次是“故地重游”,在原来照片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些。同时,最重要的是他和我都要帮助“艾克”把文章做好。艾克是第一次到中国来,一句汉语都不会,而在桂林找的几个翻译,一听说是去贫困的侗族地区,便都拒绝前往。于是阎雷只好又拍照片又当翻译,而我那糟糕的英语也迫不得已仓促上阵。阎雷拍照片的时候,我就陪着艾克聊天儿,好在艾克是一位作家,还是一个球迷,而侃文学和足球正是我的长项,于是足球便几乎成了我和艾克之间谈话最主要的内容。当我说起1974年德国夺得第十届世界杯的情景时,艾克的表情让人发笑,她大声地充满惊讶和疑惑地说:“你竟知道1974年的事!”
阎雷告诉我,一天晚上,艾克在三江县政府招待所看到电视台正在现场转播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惊讶得半天合不上嘴。
阎雷对我讲,许多外国人都像艾克一样,一点也不了解中国。而中国在对外宣传上,以及对待外国来华记者上,也确实有许多应该总结的经验教训。他说,首先,他在国外几乎很少看到中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尤其是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照片“故事”,偶尔有,也很“糟糕”。另外,许多对中国态度不友好的摄影师,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中国,猎奇,专拍一些“不好”的方面,拿出国外卖钱。阎雷说,谁都知道,在国外,说中国不好的照片都能卖大价钱,而讲中国如何如何进步的照片却经常无人问津。
阎雷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中国的坏话,因为他了解中国,知道中国的过去,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他希望用相机把中国这些年的进步与发展更多地介绍到国外。
当然,他说,中国的变革也有许多让他无法理解和“不高兴”的地方,比如一些传统文化正在渐渐丧失。最深的体会就是这次重游三江,10年前许多古朴而像梦一样的东西没有了,替代的是躁动、杂乱和传统的褪色。此次三江之行,阎雷没有拍多少胶卷,经常见他出去转了一大圈,问他拍得怎么样,他都摇摇头,直说:没有满意的画面。
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聊天儿,阎雷说:中国有许多事我也搞不懂,彩电、冰箱可以有,可为什么有的地方把自己的文化也弄丢了。法国巴黎、意大利威尼斯的许多地方还和过去一样,保存得很好,可国家照样现代化。你的文化如果丢失了,你的价值也就丢失了。
我说:你不是总说要拍梦一样的东西吗?这回,你10年前拍的东西真的都成了梦了。
阎雷沉默不语。
在三江的10多天,辛苦和劳累自不必说,过去总听人家讲外国摄影师如何如何工作,这回算是真正体验了一回,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最重要的区别还在观念和方法,在这一点,我们的摄影家与国外摄影家差距相当大。
此次采访,正好赶上侗族的“三月三”,当我们到达富禄乡(“三月三”主会场)时,已经有数不清的摄影者再次云集,有老外,当然大部分都是国内的,有广西当地的,有广东珠海的,还有从东北来的。尤其是表演“抢花炮”时,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近400名摄影者在“抢拍”。
那种场面可以想象,你已经根本无法拍照了,因为到处都是照相机,都是鲜艳的摄影背心。我说真没想到,好几年没见过这么盛大的场面了。阎雷则无可奈何地直咧嘴,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拍一样的东西。”我只好回答:“他们跟你不一样,你是来工作的,他们是来创作的,拍完了以后可以参加比赛,可以得奖。”
我想阎雷大概还不懂什么叫“创作”,一脸的疑惑,但我已懒得再给他解释。
其实,中国有许多很好的题材,但却很少有人深入进去。比如这次“三月三”,那么多人拍,可就集中在这一两天,节日一过,大家就“四散奔逃”,留下的大都是一堆似曾相识的浮光掠影。
相对比,阎雷这些外国摄影师的投入就太巨大了,这次三江之行,对阎雷来讲,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题目,但他(包括杂志社)的认真却同样让人感慨。
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早晨出发,深夜返回,还经常住在老乡的家里。独峒乡八协村是我们此次采访的重点,10年前,阎雷就曾经在这里长住了近一个月。
阎雷的老朋友、村小学的杨老师把我们接进他家的木楼。10年没见,阎雷和杨老师显得格外亲热,而阎雷带来的那本他拍摄的关于侗族的画册《歌海木寨》,更是让杨老师和村里的乡亲们“看”不释手—这是谁谁,那是谁家的小子,这不是你吗?哎,这老爹已经去世了,这个小女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这时,阎雷就抽着烟坐在一边,微笑着看着这些老乡。
杨老师说,因为阎雷这本10年前的画册和在全世界发表的关于侗族的照片故事,使许多外国人都慕名前来,尤其是八协,10年来杨老师家几乎成了“国际家庭”,已经先后有10多个国家的人住过他的家,其中有一位希腊小伙子足足住了将近1年时间。而这些“客人”回国后几乎每个人都出了书或者画册。
如今,杨老师已经“退居二线”,不再担任村小学校长,他的大儿子杨勇接任了他的职务。杨勇除了教学,现在又在刻苦钻研摄影,他说我们家来的外国人几乎都拍照片,受他们影响。当他听说我是《大众摄影》的编辑时,更是高兴,于是在八协的几天,我们几乎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也许是因为过去拍得太多了,或者是因为身体状态不佳(阎雷整天没精打采,艾克动不动就昏昏欲睡),阎雷更多的时间是在“看”,真正“拍”似乎很少,后来我们两个对了一下,他拍的胶卷还没我这个“陪同”多。
十几天的采访结束后,我们告别了三江的朋友,返回了桂林。艾克要回国,我则要继续陪阎雷留在桂林拍摄漓江山水。
3
真假阎雷
在桂林期间,我们去了两次阳朔,而这两次居然都发生了一个同样的故事—“真阎雷”撞上“假阎雷”。
一天,我们来到阳朔,下午在所谓的“洋人街”上的“红星酒吧”喝咖啡,忽然间,阎雷低声嘟嚷起来,从表情上看他很生气,而且在骂人。
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他看到了那个他最不想见的人—那个专门“偷”他的故事和想法的家伙也来中国了。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见一高大男子领着两个小孩和一个妇女,正目不斜视地从我们前面走过。
阎雷告诉我,这位专门“偷”他照片的法国人,名字叫什么格列·桑坦托尼奥,曾经跟阎雷学习摄影,是他最好的朋友。但后来,这位格列背叛了阎雷,并给阎雷留下了永远的创伤。
那是一次阎雷从哈萨克斯坦采访回来,得了一种怪病,眼睛忽然失明,格列来看他,阎雷痛苦地对格列讲,他在哈萨克斯坦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可惜自己的眼睛可能不行了。不久,格列就背着阎雷跑到哈萨克斯坦把这个故事拍了。等到阎雷把眼睛治好,格列已经把照片卖了出去,并再也没来找过阎雷。
事情如果仅仅如此,随着时间的过去也就无所谓了,关键是以后,这位格列又多次“偷”阎雷的故事和想法,包括“侗族”的专题。据说格列曾经拿着阎雷的画册专门来三江,按照画面找,重新拍,之后再发表,而文章另做,说的当然都是不好的话。
阎雷说,如果仅仅是“偷”也就算了,问题是他总是利用我的题材去做不好的事情,给我也带来很多麻烦。
我说原来你们法国人也有人干这种缺德事,阎雷说全世界都一样。
几天之后,我和阎雷再一次去阳朔,中午到“红星酒吧”吃饭,我开玩笑说,这回没准又会碰上那位“假阎雷”。没想到我们果真在酒吧里与格列“不期而遇”。这次阎雷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怨气,与格列争执起来,眼见就要动手,我和同去桂林的朋友连忙把他们分开。
整个中午,阎雷都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吸烟,脸色阴沉,饭也不吃。他说我们德国巴东人都有一个毛病,脑子里好像有一个东西压着自己,就是遇到这种背叛和小人行为,总也想不开,一定要发泄出去,否则什么事也干不了。
那天晚上,阎雷一直都在桂林的一家夜总会里跳舞,回来的时候,心情好了许多。
由于天气一直不好,拍桂林山水的计划也没有如期完成,阎雷决定返回北京。他说这次他要有一个重大的决定—他想长期住在中国,住在北京,就靠拍中国题材吃饭了。
4
家在北京
从广西回北京不久,阎雷就大病了一场。
回法国休养一段时间后,1999年春节一过,阎雷真的把家全搬到北京了。我到机场去接他的,行李严重超重,我带去的小车装满后,我们又雇了一辆“中型面包”才算把他的东西全部运回友好宾馆—阎雷在北京的家。
阎雷在友好宾馆的“家”是一套非常舒适的“中国式庭院”。他说要让所有来这里的外国人都能感受到中国的文化。于是,刚安好“家”,阎雷便首先开始疯狂地购买各种“仿古家具”和“假古董”,我说你买的大部分都是假的,他说没关系,只要好看便宜就行。
不久,他在法国的所有书籍和画册也运到了,于是他那里也成了我们这些朋友的画册阅览室,很多书都让人看不释手。
此次阎雷是以“记者”的身份长住中国,同时还作为国外四家图片社的代理,为他们组织关于中国的“故事”和“广告照片”,而这四家图片社也为他提供了全套的电脑设备,阎雷看样子确实想要大干一场了。
阎雷现在有几组关于中国的“故事”正在进行,比如“中国园林”、“中国道教”、“乌江最后的纤夫”、“康巴人”等等,有几个已经与法国《地理》、德国《地理》等达成协议。
阎雷还想拍两部关于北京的电影,他说名字已经想好了。
阎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摄影师,技艺高超,也很懂得经营。据说他为了更好地推销自己的照片,曾经专门学过两年的国际贸易,那两年的学习使他比其他摄影师更懂得如何与图片社、杂志社以及广告商打交道。
当然,“老革命也会遇到新问题”。如今阎雷也有很多让他感到“郁闷”的事—比如拍摄不太顺利:一些外国杂志出尔反尔,违反合同;同行的竞争;定单的减少(由于身在中国,许多“活儿”都让其他摄影师抢走了);租住旅馆高额的费用。
阎雷现在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必须工作,才能挣到钱。”
1999岁末的冬天,北方的大地上正是风雪交加,阎雷又背起他的大摄影包出发了,他要上华山、武当山,寻找那帮道士,开始他新的专题。
【核心提示】法国著名人文地理摄影师阎雷,20多年前在三江侗族自治县较为偏远的山区,拍摄了一大批鲜活生动的侗族生活影像。20多年后的今天,他通过浙江卫视委托晚报帮忙寻找照片中的这些娃仔,打算10月底重返侗乡与村民叙旧。22日,晚报以《照片中的这些娃仔今何在?》为题进行了报道,如今,在读者和网友的帮助下,相片中的多人已被找到。
箩筐中的兄弟找到了
“照片中挑在箩筐里的是我同学。”在三江县城工作的吴先生看了晚报的报道后,当即拨打热线提供线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是三江县独峒乡唐朝村的,被挑在箩筐里的是一对兄弟,挑担的是他们的母亲,也是唐朝村的,“照片中的风雨桥,目前还在。”
25日下午,记者与坐在照片中左侧箩筐的阳先生取得联系。他告诉记者,他今年27岁,弟弟比他小一岁,当时他母亲是从外婆家回来,因为他们当时都还小,也就两三岁,母亲就用箩筐挑着他们回家。
“他们把照片发给我,我就拿给母亲看,母亲看了照片就想了起来,印象很深。”阳先生说,他母亲现在身体还可以,他和弟弟都成了家,都有了小孩。这些年,村子变化很大,公路修到了村里,很多村民都建起了楼房。目前,弟弟在广东打工,而他过几天也要离开村子到广东打工。
“印象中,阎雷在我家住过。”在南宁工作的杨先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是三江县独峒乡八协村的,1989年,他读小学的时候,他家里住了个外国人,好像就是阎雷。1992年的时候,还有个丹麦的外国人在他家住了差不多一年。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到杨先生的哥哥杨勇,他向记者证实,1989年左右,阎雷确实在他家住,当时他正在师范学校读书,印象很深刻。他说,阎雷的中文很好,他们都是通过中文与阎雷交流的。目前,他正在村上的小学做老师。对于阎雷重返侗乡,他表示欢迎,“这些年,侗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欢迎他再次来感受。”
网友留言赞赏阎雷和三江的变化
除了向晚报提供照片上人员的信息外,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赞赏阎雷是个优秀的摄影师,以及感慨三江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
网友“杨胜文”留言:“箩筐里的两个男孩是我们村的……”“那个挑着箩筐的妇女我认识,是我们村那里的人,如果没猜错的话,那两个小孩就是他儿子,也是我同学。”
网友“乖乖”:“吹芦笙最清楚的那两张面孔是我同一个寨子的,现在他们都老了。”
网友“长发琯君心”留言:“据说这个摄影师的蛮多照片都是精品。”
网友“秋雨”认为阎雷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摄影师”。
网友“大哥”留言:“他已经走了80多个国家,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地理摄影师,他一直在路上……”
网友“eliza”:“希望能找到这些曾经的面孔,20年后再重逢,多有意义啊。”
也有网友留言宣传起三江来:“我是三江人,20年里,三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江越来越美,是个休闲旅游的好地方。”
网友“行行摄摄”:“真佩服,真心学习中。”
网友“呼呼作响”:“哈哈,八协刚好是我的家乡,桥的确是八协村的桥,现在家乡变化大了,家家户户种植茶叶,公路两旁到处都是茶叶加工厂,到处是砖房。”(记者李书厚实习生张琰笑)
法国著名人文地理摄影师阎雷于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三江侗族自治县较为偏远的山谷,拍摄了一大批鲜活生动的侗族生活影像。20多年过去,他很想知道被他摄入镜头的村民而今的生活状况,于是重返侗乡与村民们见面叙旧。![]()
阎雷这样回忆他在三江侗乡度过的半年生活:“在距离我所认识的那些时髦艺术家们几千英里远的地方,我感觉到自己终于离中国的真实世界更近了……我在这边远的山区摆脱了时事的干扰。这里的山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此前从未有外国人涉足过!”
当时帮助阎雷和侗族人交流的向导名叫天宝,他是当地唯一的老师。天宝告诉阎雷:侗语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声调语言。汉语只有四个声调,而侗语有十多个声调。生活的欢乐和悲伤都被编成四十四种不同类型的歌曲来表达,有情歌,酒会歌,上山歌……